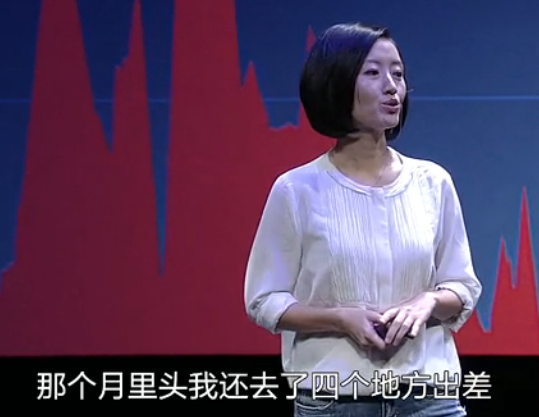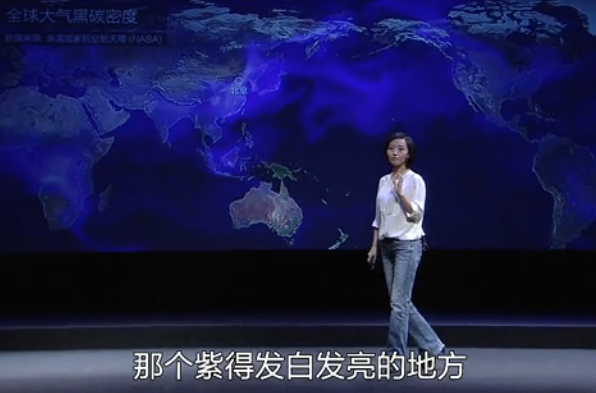谢谢你医生《这次,不谈杨幂,谈谈作为病人的亲身经历》
- 电视剧评
- 2023-03-26 02:08:23
- 63
老实说,一看杨幂,我第一反应是拒绝的。这位女明星实在演过太多我本人想拒绝,但平台无限推流到我面前的剧了。
然后,我打开豆瓣,看到热评里出现了友邻曾于里老师的剧评: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这十二个字有点戳到我。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是我们老实人欣赏的品质。这句话也令我想到丁香医生那个平台“偶尔治愈”,我有老同事曾在此供职,也是在上面看到过一些好文章的,于是选择进入这部剧。
再老实说,这个开头也很劝退我。
战地求婚,明显后期配的英文,略显做作的演技......我大概就是当扫地背景音在播放。但本着如毛尖老师那般“我为人民看烂剧”的义勇,我继续观看。
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被触动的呢?
大概是沈沛海和他的夫人夏清韵告别那里。这个情节相比前后的病例都显得不那么戏剧性,老人跌倒撞到脑袋,因为年纪大承受不住手术而离世。而患者本人和家属都是医务工作者,也让这件事似乎多了一些理性上的可接受,直到沈沛海出院时,从自己卡包里掏出老人卡时,突然意识到老伴的离开顿感悲痛。
白术对他说,打个的士回去吧,沈沛海说:不赶时间,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已经没有老伴了,坐的士和公交车有什么分别呢。
这段台词大概是第一次击中我的地方。再赫赫有名的医学专家,也要面对生死,也要面对最终一个人踽踽独行的终局。而后,就是肖砚和白术那段堪称经典的对话:
白术之所以当医生,是因为相信医学的确定性,于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肖砚则认为,医学归根到底是人学。
我并非医学生,这个探讨大概也没有对错,如题,今天我想说的还是自己的经历。
今年3月末,我左眼突发视力问题,表现为视物中心模糊,有一小块灰色遮挡。因为本来就是高度近视,每年都定期随诊,当时心里紧张得不行。第一反应是就近去看了朝阳医院眼科,一位副教授替我看诊。这位大夫性格非常随和,也嘱咐我随时来医院观察。当时我每天一早先在一楼打维生素B的营养针(护士说是营养神经),而后上眼科在眼周注射,差不多打了两周。打到护士都纳闷:你是啥病啊,咋还没好?
彼时,我治疗两周,病情不明,怀疑黄斑水肿,左眼视力只有0.5.
两周治疗不能确诊,视力毫无恢复,我当时真的面临一种巨大的恐惧。而让这种恐惧加重的是两周后的一天,我的主诊大夫跟我说,怀疑黄斑其他问题,让我转同仁或者协和看看。
一路辗转,我同时挂了协和和同仁的眼科。
然后,我在同仁的经历可以说如堕冰窟。我上午从朝阳出来,就立刻到同仁现场挂了一个最近能看到的眼科特需,医生面无表情地替我诊断,初诊黄斑出血。翌日,我又去影像科做OCT等一系列检查,医生同样面无表情地没有对我的病情做任何分析。
当时的心情,恐怕只有生过病的人才能体会其中无助。我的表哥是呼吸科医生,现在林芝援藏,我属于医生家属,已经属于人群中对医生多有体恤的人,但当自己作为病号,那种无助仍然无法形容。我清楚地知道,同仁的医生已经做到了自己本分,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但当时的我真的非常需要安慰。黄斑出血,是一种眼底重症,需要眼球注射治疗,不仅手术费昂贵,而且仍有失明危险。
不巧的是,我在同仁的复诊号和协和撞在同一时间,当时我万分纠结。因为很多医院只认本院报告,如果我去协和,又要重新经历一遍检查(眼科检查并不好受),而如果留在同仁,我的心理压力仍未减轻。最终,表哥替我拍板,去看协和的眼科主任,放弃同仁的眼科副教授复诊。
知乎上有个问题叫协和的大夫到底有多神,此中答案大家可以自己细细去看,但对我来说,协和确实意味着某种确定的安全感。
作为每年都去定期报道的大近视,好几位大夫我都很熟。我之前常看的一位大夫很儒雅,说话慢条斯理十分温柔,见我一个人报道,还嘱咐我观察期不要走开。我后来偷偷看了他的介绍,他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博士,后来也去援疆了,好几年后才回来。
有一次,想去咨询高度近视的手术,挂了一个女大夫的号,后来因为赖床没能起来,竟然接到大夫的电话:xxx,你今天怎么没来看病?当时有种被班主任抓包的小学生感,但是意外地很安心。
还有一次,我妈妈作为家族大近视之一,视力持续低迷也是查不出原因,我灵机一动,去挂了个号问协和的医生,这位大夫发量堪忧(对不起23333)但为人也十分和善,当我说出我妈的问题时,他微微一笑说:有可能是白内障。然后,我妈就南下治病去了,果然在中山眼科确诊了白内障。
总之,此时已经辗转一月的我,来到协和,不知怎么,有了一种安全感。
很快,做完检查后,我确诊了。不是黄斑水肿,也不是黄斑出血,而是白点综合征。
这种一种病因与HPV类似的眼部免疫力疾病,主要由生活作息不规律、免疫力不高引起。主任开了一支不到十块钱的注射剂,一瓶维生素c,两瓶眼药水。
我当时有点哑然:就这?
折磨了我整整一个月的眼部问题就这?为什么之前每个医院的确诊都不一样?有一种剧情都烘托到这儿了,怎么也要让我住半个月院,结果通知就地下床的感觉(bushi
主任颇有威严,但是面对求知若渴的我还是解答了:每种疾病的诊断都没有金标准,每个医院也都不一样。他没说我之前打的针不对,只是说了一句:你要想打呢也可以。护士无限同情我眼睛旁边被扎了半个月的针。
anyway,到此,我的看病之路总算走上正道。
然后是每隔一个月复查,然后两个月,然后三个月。五个月之后,在协和大夫的严密监控下,我终于康复了。
这几次复查我也在诊室里见识了一些主任看其他病患的现场。比如有那种眼压很高,担心青光眼失明的;比如有那种玻璃体出血,急着做手术的。主任的答复通常是:现在没有问题,回去观察。叫你来你就来,不叫你来,你就正常生活。
又或者:
我也玻璃体混浊,这个老了没有办法的呀。不影响正常生活。该生活还是生活(摊手状
遵医嘱,来医院,担心的事交给医生,你平时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作为公立医院的医生,他没必要提供情绪价值的,但是作为病人,因为他多说的这几句话,真的能看到那一点光。
说到这里,我的亲身经历终于拉拉杂杂地说完了,想必看的人也知道了我的立场:作为病人,我当然觉得医疗是一门人学。因为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具体的人,相关到具体的家庭、感情、工作、生活,当医生身处这些其中,如何能不被这些“人事”影响。
有一次,我在旁边听到主任和他的朋友打电话,说到自己女儿,大概女儿也是一位医生,刚刚学成归来,老父亲颇与有荣焉,在办公室里忍不住得意地翘起了脚。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老父亲。
当然,作为医生家属,我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医”,这是学理,也是技术,只有技术够好,才能帮助病患,否则再好的态度,再好的服务,都是无谓。不过,能够做到技之外,将医学作为人学的医生,真的更棒——因为他们做到了本来没有被要求的医者仁心。
治愈很重要,帮助和安慰也同样重要。
谢谢你,有仁心和有帮助的医生。人类闪耀,莫过如此。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02:08:23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本文链接: http://www.w2mh.com/show/8893.html
 小小评论家
小小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