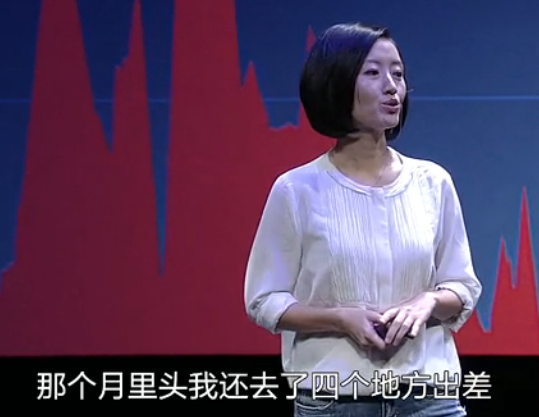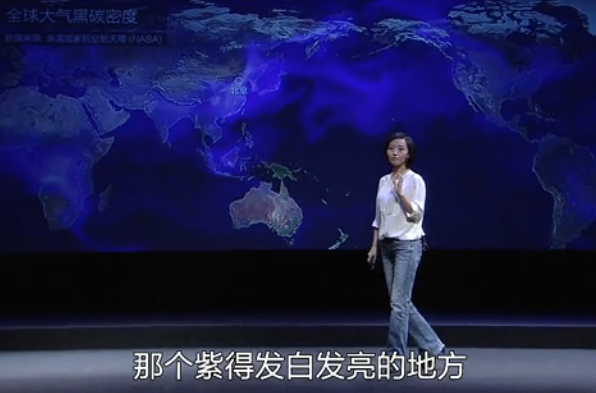来自深渊:烈日的黄金乡《深渊与乡愁》
- 电视剧评
- 2023-03-26 01:07:06
- 111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既是《来自深渊》的看客,又是提瓦特大陆的旅行者。游历提瓦特诸国期间,凯瑟琳的那句“向着星辰与深渊”,已然成为我心中作为冒险家和探路者最激昂振奋的宣言。将星辰与深渊并列,使得这两个本就震撼人心的意象交织起来,彼此成就出更高层次的意味。而这个交织而来的意味,我认为正是《来自深渊》系列的核心理念,是那些震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的情绪压抑、晦暗、悲恸,让我们的灵魂战栗、颂赞、呐喊,一次次引我们头皮发麻的根源所在。一、星辰与人心统一于无底的深渊康德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物,我们越是付之以坚持不懈支持以恒的思考和探索,它就越是带给我们日新月异历久弥新的震撼和感动,那是我们头顶之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尼采说“凝视深渊,深渊必回望以凝视。”
无边无垠的寰宇,深不见底的人心,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人在世间最重要的隐秘,于是,超越已知的边界向着无垠的未知探索、跨越道德的藩篱不断叩问人性人心,这两种活动就成了人世间最伟大也最危险的探秘,并且,这两种危险往往是相伴相随的,那种迫使我们刺破伦俗、凝视人性深渊的情境,往往是在人类远离安稳熟悉的文明之地,行至蛮荒时出现的,黎明卿作为开拓者的所作所为,以及全部白笛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甚至可以说变态的),都可以作此理解。
而这两种隐秘的意象、这两种探秘的活动、这两种伟大与危险,在《来自深渊》的故事设定中,被巨洞“阿比斯”这个符号深刻的、完美的、近乎天衣无缝的结合起来了!行向深渊既是对未知的探索,又必然是对人性的突破,两个过程相互交织,互为背景,在每一层冒险的生离死别与道德纠葛中,探窟者为了潜入至深之处,不断从身体与心理上谋求对“人”的超越,以神性与***掺杂的“非人”发起对世界的挑战与征服,奏响“属人”的悲歌与赞歌;这样的设定,是神作之为神作在开局处的“神来一笔”。二、深渊与乡愁统一于虚幻的驻留
《来自深渊》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烈日下的黄金乡》作为续集怎样推进、升华了故事主题,我就讲一个自编的寓言吧,这个寓言本来是为了阐述尼采的理念,和《来自深渊》的故事也很相像。让我们设想一口深井(我比喻的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或者说宇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冷酷漠然,它就是存在于那里,没有什么目的,不为什么价值,它天生的规则,比如说,就是东西要掉下去(脑子里开始自动播放gravity gravity gravity囧),那么死的东西会摔碎,活的东西会摔死,而世界——这口深井也压根不在乎这些,不在乎从自己的崖壁上生长出来的花草虫子,偶然诞生的它们和石头一样,没有高级低级的分别,所以不管你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东西是有意识的,有智慧的,还是本能的······这井只是深不见底的存在着,永恒沉默着,冰冷默然地吞噬着。然后,就有一些家伙,用墙上生长出来的花花草草编织一张美丽的网,把井盖起来,他们在花草编制的美丽的地毯上生活,让所有人相信,这个地毯铺就的,就是我们的世界。然而,他们最后当然会发现,网是编造的,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尼采说,“把网撕碎吧!让弱者掉下去,超人就是要每天直面着深渊,在崖壁上生活,为自己订立生存下去的目标与价值!这样的生命才能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这个讲述尼采理念的寓言,在什么地方与《烈日下的黄金乡》关联呢?就是那个网,那个用花草地毯编织起来的网,正是来无回之都中的“惨剧终末之村”,咿噜缪咿的化身。
“罡甲”的全部成员,是一群被家乡抛弃的人,他们循着罗盘去往孤岛,深入巨渊,本身是为了“寻乡”,表面上看,这和“向着星辰与深渊”的探索精神似乎正相对立、截然相反!但这种对立只是表象罢了。
象征前进、探险的罗盘,让瓦兹强感到的却是“思乡”,这两个看似相反意象的内在统一,这里已经表达出来了。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一路向着深渊的故事主角们,反而和故事主题一道,被设定为“来自深渊”,如果黑暗的深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宿命般的、不可摆脱的召唤,那它已经作为“乡”拥抱了我们的灵魂——这种必然去往的地方,也就成了规定我们的本质,继而在逻辑上倒转过来,成为我们的根与源,于是一个讲述奔赴的故事写作“来自深渊”了。
深入一点来说,其实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开拓者,无论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开拓者,还是知识思想领域的开拓者,他们大部分都是一群和我们常人所居“家乡”格格不入的出走者,他们孤独流浪的路途看似是勇往直前永无止境的,他们的前进似乎只以前进本身为目的,但这其中支撑着他们的往往正是一种“乡愁”,一种对陌生远方能给我心安归处的憧憬愿望。罡甲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不断前进着,并在行将崩溃之际找到了那个“家”,能够把他们在跋涉中破碎殆尽的尊严、执著、道德感全部捡拾起来,把面向彼此的爱与牵绊、自己内心深处的留恋与信仰,重新注入灵魂,慢慢修复疗愈的家。这个家就是他们孜孜以求的“黄金乡”啊!
所有人都这么想着,相信着,但唯有这个“家”的缔造者,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不是,绝对不是。瓦兹强看到了最远的地方。
瓦兹强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这群人心中涌动的不是一种因放逐而生的寻觅,而是那种终极的“乡愁”,而这种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状态并非以逻辑上的曾经“在家”和“离家”为前提,能至深感受这份“乡愁”并受此驱策的人,他们的无家可归是先天的、终极的,也是永恒的,故乡以一种“曾在”的亲切感召唤着他们,却没有可以归去的地方,只能导向不知终点的“去往”,这就意味着一旦上路就不会有尽头,他们的“黄金乡”,就是永恒的“在路上”。
所以惨剧终末之村只是那个花环编织的、盖在深渊之上的网,它有着近乎完美的社会形态和价值体系,那种可以关照到每个人内心真正欲望并等量齐观加以衡量的能力,形成了一个远比我们现实中价格均衡体系更平等更正义的市场,在市场中进行交换所依凭的价值不是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交互形成的抽象的价值,而是依凭着发自内心的价值的本体,交换的双方也就达到了灵魂层次的真正的“等价交换”。但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社会,完美的道德,和历史上曾经一切美好的编织一样,隐瞒着建立之初的血腥残酷,用美好的一面朝向世人,充当一张又一张盖住深渊的网。
这一点在故事的另一个核心设定中体现的更为明显,那就是深渊的“上升诅咒”,它意味着文明发展的单向性,文明只能向前,它可以在向前的过程中被自然力量所杀戮,在内部纷争中自我毁灭,也可以在永久的停滞中衰老、自我瓦解。但它唯独不可能调转头来,不可能“回到童年”。越行至深处,这种回头就越发困难,农耕社会退回渔猎社会意味着剧痛,对于现代社会那只能是毁灭。所以每一层就有每一层的挑战,在不同的层次上驻留也需要不同样态的“虚幻之网”,咿噜缪咿化身的终末之村在六层以前是建不出来的,在六层之下也绝不可能,它是人类下潜至这个层次所专有的样态。
随着深渊的诅咒被隔绝在外,村子的规则覆盖了深渊的法则,村民们(假装)忘记了深渊,既忘记了它的危险,也忘记了它的伟大,最重要的是,那些定居下来的建立者和后来的探窟者都假装着,对自己灵魂深处最初的呐喊视若罔闻了。
但瓦兹强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践踏道德和人心建立这个村子时就知道。这个“家”只是为了让无以为继的罡甲停歇下来,在建构的美好中修复破碎的信念,积蓄直面深渊的力量。并且,他深刻的知道,所谓向渊而行,人们将永远地、不断地重新面对他们在初临来无回之都时的境地,失去前进的力量,甚至需要舍弃一切道德和尊严来维系自身的存在,用残酷的逻辑和血腥的手腕奠基、编织虚幻美好的“家”。
为此,他需要这样几个要素:
首先,他需要完整的三贤,他深知自己这种绝对理性而无比深刻的智者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绝对高尚的、在一切新生秩序奠基时能够赋予其合法性的道德权威(贝拉芙首先投入咿噜缪咿的怀抱,众人紧随其后);需要一个能够跟成员共情、尤其是同需要牺牲的关键成员形成羁绊的、往往以保姆般姿态存在的仁者。这二人结合起来意味着:瓦兹强为了前进所抛弃和践踏的一切事物,都会经由二贤在群体中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完整的三贤隐喻着人类作为一个文明,以群体挑战深渊所必须具备的三种特质。
第二,瓦兹强需要这个“家”存在敌人,这个虚幻之网只有在编织之初,凭借的是深渊本身的、残酷的逻辑,在那之后它就以虚构的美好为内部的规则了,从而让人们忘记了深渊的存在;瓦兹强需要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被虚幻美好所遮蔽的血腥历史的背负者,以毁灭者、复仇者的姿态出现,她在唤回织网的残酷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就唤回了人们对深渊法则的感知与觉悟,这个分化出去的异己的、敌对成分,成为文明僵局的突破者,从灾难成为革命。
最后,上述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贝拉芙和布耶可的坚守和执著,能够整合容纳分化出去的破坏性力量,不至于最终走向彻底毁灭,而真正实现破而后立。在剧情中表现为法普妲接收了贝拉芙的记忆、感知了布耶可的情意,达成了某种释怀,而受到两位贤者不断引领的村民们始终具有一种超越生死的情怀,把这个意图毁灭一切的公主,视为罡甲的延续献出己身。
最终,三贤的品质、变革的力量、时代的积累、康复的罡甲,在法普妲这里重新统一起来,与莉可三人组一道站在传承的尾端,再次迈向深渊。而那无底深渊的深处,相似的、永无止境的驻留与上路还会一次又一次上演,在那样的无尽中,他们会与瓦兹强预言的绝望相逢,或者凭借自己的力量突破它奔向下一个绝境,或者失去了前进的力量编织出下一张酝酿风暴的虚幻之网,或者倒下了,成了不具名的白骨。但罗盘还在那里,还会有人捡拾起来,行向深处,永恒地怀揣着谬误的信仰:在那没有尽头的尽头,存在着不存在的黄金乡。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01:07:06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本文链接: http://www.w2mh.com/show/6190.html
 小小评论家
小小评论家